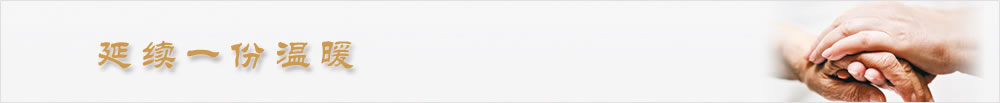
msn上的米老排,永远停机了......

很久不见米老排上msn了,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上,尽管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,但是我还是不相信,总想着过几天给他打电话,还能听见他爽朗的笑声。
今天实在忍不住,拨了他的手机,已然停机了。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要来,我给一位跟他熟悉的本家妹妹打电话,也停机了,给她msn留言,让他看到尽快帮我打听老排的消息,或许他随父母回乡疗养了。
最后还是忍不住在Google搜了一把,因为有很多朋友给都在关心他的健康。搜出来的是他的导师许纪霖先生、程映芳教授的给他的悼文。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
我认识老排是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,彼时我在上海,当时华师大发生了一件"校门事件",闹得沸沸扬扬,单位让我去采访,而米老排则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者。
我给米老排留言,然后网上聊天,理所当然的,我的稿子被戴上了和谐口罩(那时候应该是戴了3个表的),但是和老排却成了朋友。
在老排灿烂的笑容里,其实很难想像他是一个骨癌的病人。但是聊到深处,他还是很清楚自己随时都会"挂"了。米老排是一种耐火的林木,常被种植做防火林,显然,他也希望自己跟米老排一样烧不死,生命长青。
2004年的春夏,我因病前后有几个月赋闲养病的日子,那也是我跟米老排来往密切的日子,我去华师大看过话剧,在他家里吃过他炖的鸡汤,还参加过他的一个party。
在灿烂的笑容背后,他还是藏不住对死亡的恐惧,这让他对任何爱情都犹豫不决。于是我做了他的爱情后援团,出谋划策让他去追心仪的女生,那是他每个字里都蹦着笑声的日子。
某次,我在华师大校门口遇到一个卖大刀的,西北兵工厂出来的80公分长钢刀,于是买了一把。晚上八九点站在黑乎乎的马路上等他接我去他租住的房子喝酒,他见我笑了好久,说我像个劫道的,像个戴眼镜的张飞,问我有没有收到买路钱。
那年冬天我搬家的时候,他还来帮忙搬东西,并且拎了鞭炮来冲一年的晦气。2005年6月,我离沪北上,他也曾专程来送我。随后他入许纪霖先生门下,成为许先生的博士研究生。
在北京我们还是经常msn聊天,他是那种博学、善良,内心一团阳光的男人,跟他聊天也是快意的事情。再到2006年春夏,老排说他要动手术了,这次可能要挂了。我大悲,在新闻评论部四楼的洗手间失声痛哭。每天担心噩耗会传来,所幸他手术很成功,并且很快出院。
2006年10月,我去杭州出差,专程绕道上海,在徐汇医院的肿瘤病房看他。当我捧着一束百合出现在肿瘤病房门口的时候,他的笑声又起来。
当时他经过前后几次手术,多次化疗,头发已经全脱光,显得脑袋很大,眼睛深陷,手也显得干瘦,且有些冰凉,与16个月前迥然两人。我让他使劲握我的手,还有一些力气,我说劲儿挺大嘛,下次我回来可以一起去踢球了。
但是彼此都知道这种可能已经微乎其微,尽管前一年他手术切除了肿瘤,但是癌细胞已经向骨髓扩散,只能靠化疗了遏制了。死亡的阴影,生命深处的痛楚已经不能碰触了。
于是我们开始东拉西扯聊别的,其间他服药一次,当时我想给他买饭,他已经不能吃外边的东西。
大概不到一小时,因为不想打搅他休息,我起身告辞,说了些祝他早日康复的话,有时间出差我还会再去看他等等。我退着出门,看着他瘦弱的身体,尽量用笑容和他作别,退到门口时扭头向外,眼泪已经唰唰的下来。
此别已成永诀,2007年2月28日,我亲爱的朋友米老排悄然离世。
2003年我给一位仙逝的长者写悼亡的文字,米老排说淡淡地说没准哪天就是我了。我想起苏轼的诗句,已约年年为此会,故人不用赋招魂,心中凄然。
已约年年为此会,故人不用赋招魂,天地曾不能以一瞬,况乎人?然斯人已去,终归要文字记下我们的交往,留下彼此生命的印迹,并且随着我们的生命灰飞烟灭。
|
电话:010-81181138 | 地址:京藏高速水关长城出口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东侧 | 邮编:102112 | 京ICP备2020044598号-1 | 技术支持:八达岭陵园网络工作室 |

